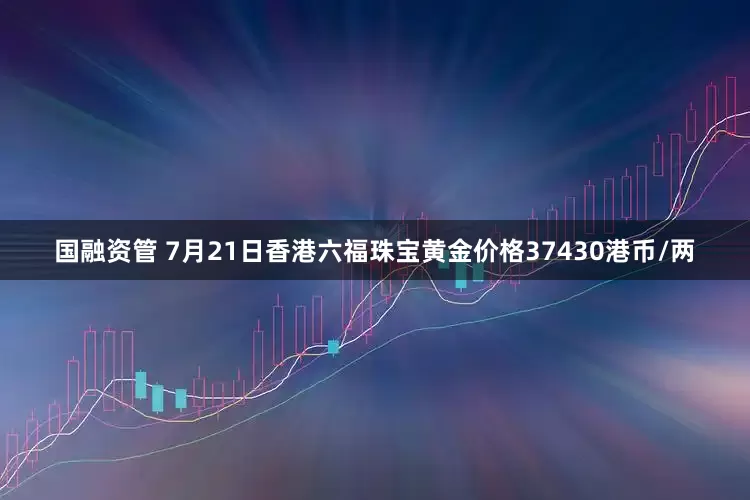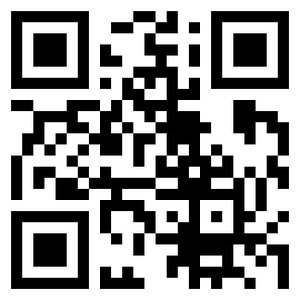沈醉在《回忆录》中提到,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“四个惹不起”的人扬帆配资,虽然他没有直言不讳,但从他提供的部队番号和个人履历,细心的读者可以轻松地推测出这些人是谁。那四个“惹不起”,表面上看似威风凛凛,实际上不过是对战犯互相打压罢了。面对管理人员时,他们不过是像绵羊一样温顺。所谓“惹不起”的其实只是他们利用对同伴的压迫来换取更好的改造评价,以便在特赦名单中能抢个先机,早些出去。
但在功德林,除了这四个“惹不起”的角色外,还有更令人头疼的存在,那就是“刺儿头”。这些人,或是阳奉阴违,或是固执己见,想要把他们从内到外改造好,简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说到这些“刺儿头”,那些看过《特赦1959》的读者,肯定会立刻想到徐远举和周养浩这两个名字。没错,这两位就是典型的“刺儿头”。事实上,《特赦1959》更像是一部纪录片,剧中的化名人物,如刘安国、叶立三、蔡守元等,几乎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历史原型。比如,刘安国的真实身份是曾经担任过军统中将的文强,叶立三则是被俘的七十三军中将韩浚,而蔡守元则是“罗盘将军”张淦。
展开剩余76%蔡守元(张淦)的表现积极,甚至立下赫赫战功扬帆配资,但因为他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发布前便因病去世,未能出现在特赦名单中。蔡守元当然不是“刺儿头”,而叶立三(韩浚)也不是。韩浚在1931年便被纳入第三批特赦名单,这也证明了他在改造过程中的表现得到了认可。毕竟,像文强这样的复杂人物,若表现不佳,怎能那么早就被特赦呢?
与此不同,周养浩和徐远举的表现就截然不同了。这两人罪大恶极,且在被捕后依然不改悔。周养浩怀疑沈醉揭发自己,因而曾动了杀机,甚至亲自下毒。沈醉亲自目睹了这一切,而徐远举更是典型的不认罪分子。尽管他被抓后表现得有些低调,但在看到第一批特赦名单后,他却大喊大叫,坚信自己应该列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中。沈醉对此也很不满,他本可以通过沈醉的提携得到“提前出狱”的机会,但这一切却始终无法化解他心中的不甘。
沈醉自己也深知自己有不少罪行,尽管这些罪行不如周养浩和徐远举那么严重,但也足够让他付出代价。他坦言自己在担任保密局云南站少将期间,参与了不少冷酷无情的行动,尤其是“九九整肃”,更是让他在抓捕时丝毫不顾人道。那时,沈醉甚至要求看守所腾出空间,将几百人关进狭小的房间里,“不让他们睡得舒舒服服”,这足见其冷酷无情的性格。
而徐远举和周养浩这两个“刺儿头”在管理所中的行为并没有真正改变。徐远举因不满意工作质量,竟因一件缝纫不合格的裤子大发脾气,而周养浩更是伪装自己直到1975年才被特赦扬帆配资,出狱后立即准备跑去台湾与蒋中正联系。若不是老蒋当时身体状况不佳,恐怕周养浩的所作所为难以想象。
此外,文强和黄维这两个“刺儿头”的坚硬态度,也让管理人员很是头疼。文强一度拒绝书写认错材料,黄维则以研究永动机为借口,不肯承认错误。沈醉曾在回忆录中提到,黄维在批评时常常沉默不语,甚至在不耐烦时,竟用“放响屁”来应对,这令沈醉忍俊不禁。
然而,黄维在特赦前,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。在特赦那天,他终于表态:“我早就下定决心了,不去台湾,不出国,唯一的愿望就是留在大陆。”同样,文强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:“我不去台湾,也不出国,我只希望能定居大陆。”文强和黄维的态度与周养浩和徐远举的态度有天壤之别,后者只是装作“积极”,根本没有悔过之心,而前者则是真心悔过,虽然一开始不肯承认,但在最后终于表明了心意。
文强和黄维最终都在特赦后留在了北京,担任了政协文史专员,享受了相应的待遇。两人也在多次历史事件中担任了重要角色,参与了追悼会的筹办和守灵等任务。这一切都表明,尽管他们走错了路,但他们最终选择了回头,与徐远举和周养浩的“不悔改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,四个“刺儿头”的故事让人深思。它们不仅展示了不同人物在面对同样境遇时,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,也揭示了人性中复杂的一面。您是否也有自己的看法呢?如果让您来决定这些人的是否特赦,或者特赦的时机,您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?
发布于:天津市捷希源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